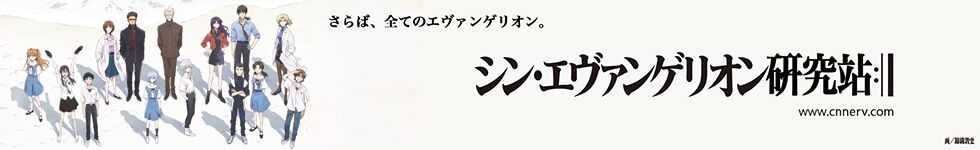燥热夏日里的河水被午后的夕阳染成了血色,血色河水中现代文明的废墟时隐时现。河岸的巨石上端坐着一个挺拔的少年;温柔地望向血河的另端,目光坚定而又执著,仿佛看到了充满幸福的彼岸,脸上露出了一丝迷人的微笑。
二、褚薰与罗伯斯庇尔——达摩克利斯长剑
人类对物质需求似乎是永无止尽,在追求现代化、实现文明、摆脱愚昧的过程中不断破坏着自然和赖以生存的环境。对人工环境的依赖也越来越大,对不多的物质的争夺也越来越加剧。自私自利的现代人更是越来越不知节制自已的欲望“随心所欲”成了我们的理理和追求,而无视于大自然的痛苦。“性解放”被惯以精神文明,“竞争意识”成为社会优良的象征。启蒙哲学无神论的继承者们,在宣判上帝的死亡的消息之后,财富的聚集者们便迅速展开了新一轮更加放肆疯狂的掠夺和破坏。各种核武器、化学武器也以难以预料的速度竞相出现。水灾,地震,火山爆发,新的疾病,物种变异,食物链的破坏,这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无法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。只有卢梭——这个在森林中孤独的“少年”,二百年前发出了来自上帝的呐喊。首先提出“人生来是善的,是文明引起道德的败落。可悲的革命带来了冶金术和家耕;五谷是我们灾难的象征。”“我们幸福,来自已身?还是来自别处?”;“一个人在他一生的某个时期必须把他所接受的所有教育——全部偏见,像呕吐宿食一样呕吐干净。”;“回到自然中去吧,野蛮人(自然人)和自然万物和平相处,跟所有族类友好不争。”然而,愚蠢的人们却把他当作疯子看待,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活埋了他。
在他死后不久,一个年轻人手持达摩克利斯长剑,悄然走到大众面前,以纯粹卢梭风格的语言起誓:----“当未日审判的号角吹响,看有谁敢于对您说:‘他比我更像您,卢梭?’”----这个人就好象《使徒书》中的使徒。要将所有被人类视为糟粕的道德重新拾起。他的经历与少年时的卢梭惊人相似,6岁时,母亲难产去世。8岁时,父亲患漫游症,消失不见。年少的罗伯斯庇尔也养成了内倾式性格。常常一个人陷入沉思,仿佛只有他一个人。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;1793年罗伯斯庇尔代表的雅各宾派上台;人们开始传诵一首颂歌“啊,美德!你是一把短剑,你神圣的尖刃 是大地唯一的希望。”自此,巴黎开始经受革命道德清洗。启蒙遗老与所有背离道德的人一样遭受逐杀。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的弟子全无幸免。一个声音在血腥的空气中回荡,“反对卢梭者,不是阴谋家,就是人民的敌人。他们曾忌恨并阴谋迫害过卢梭,他们都该地狱。”1793年12月(霜月),94年7月(热月),人们感叹“塞纳河水太红了”。罗伯斯庇尔反驳道,“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的,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。”;1794年6月,‘牧月嗜血’开始,死神开始召唤非特权阶级和下层人民,一时间巴黎广场被血水染红了!;7月,罗伯斯庇尔被叛徒们杀害。瞬时,短暂而恐怖的杀戮嘠然而止。死前,这个曾执掌达摩克利斯长剑的使徒,一语道破了天机:“我只知道有两种人,正直的人与邪恶的人。爱国主义不是政治问题,是心灵问题,谁能作出这种区别?良知和正义。 我说的是什么?美德,没有美德,一场伟大的革命只不过是一种乱哄,是一种罪恶摧毁另一种罪恶。拿走我的良知,我就成了一个可怜的人。”
褚薰和罗伯斯庇尔的出现同样是处于这样一种人类无秩序的状态下,以正义的使徒身份,来审判正在一步步逼近歧途的人类。因此才对人类的存在形态提出了发自灵魂的质疑,“EVA所创造出的人类,究竟是怎么样的存在价值?”“如何利用这个来生存的?我真不明白!”“亚当的存在就象是母亲,亚当创造出来的东西就应该归还给亚当。就算是人类毁灭也要那么做。”“生和死是同等价值的
。自已控制死亡,才是唯一绝对自由的。”
《圣经》中,上帝说:“我要回来的;在我回来的时候,我要毁灭这个世界!”
(未完待续)
终篇:三、人类的归宿————死亡是不朽的开始。
真嗣:“那么,我的梦想在哪里?”
‘那是现实的持续。。。’;
真嗣:“我的,现实在哪里?”
‘那就是梦想的结束。’.